MK体育官网 MKtiyuguanwang 分类>>
马来亚战役:日军靠的是自行MK体育- MK体育官网- APP下载车还是坦克?
MK,MK体育,MK体育官网,MK体育app,MK体育网址对马来半岛的入侵及随后向新加坡的推进,可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装甲部队作战的巅峰。1941年12月8日,日军以海岸炮击拉开进攻序幕,随后精锐的第十八师团在马来亚东北海岸的哥打巴鲁登陆。与此同时,第五师团先发制人,迅速占领了泰国东海岸的北大年与宋卡,打乱了英军的防御计划。被日军抢占先机的英联邦部队,只得退守至靠近泰马边境、位于马来亚西海岸附近的筑垒阵地——日得拉防线。日军对日得拉防线的情报掌握甚少,这意味着他们的推进将危机四伏。为了抵消这一风险,以第1战车联队第3中队为核心组建的佐伯支队被派遣至战场,伺机突袭英军防御体系的任何薄弱环节。

▲日军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推进作战示意图,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

佐伯静夫中佐麾下的这支小型部队包括两个九五式轻型坦克中队、一个九七式中型坦克中队、两个摩托化步兵中队、一个工兵小队、一个医疗分队及一个通信分队。该支队特定任务是突破位于河谷以南的宋卡公路防线。成败完全取决于快速机动——这个致胜的要诀被指挥坦克先头部队的山根稠中尉(第1战车联队第3中队中队长)深刻领会。战前他曾斩钉截铁地表示:“若有一车瘫痪,弃之续进;若有二车停滞,舍之前行。纵需碾压敌友,亦当推进至最后一刻。”
12月11日下午,以佐伯支队为先锋的日军进攻撞上了据守英军防线的印度部队。从未遭遇过坦克的印度部队顿时陷入恐慌。指挥英联邦部队的默里-莱昂少将请求撤退到日得拉以南不到五十公里处,位于牛仑天然要塞内一处更易防守的阵地。全面指挥马来亚英联邦部队的阿瑟·珀西瓦尔将军拒绝这一请求,因为如此早的撤退会对士气产生不利影响。在珀西瓦尔看来,除了守住日得拉防线别无选择。


▲正在为炸毁马来亚半岛桥梁而设置炸药的英军工兵,此类行动成为延缓日军推进的关键战术,亦是英军在整个战役期间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在日军推进过程中,坦克始终冲锋在前。坦克炮火既能将防御阵地撕开出缺口,又能有效地压制敌军火力。在日得拉,以非常规战术投入战场的日军坦克成为高效的战斗力倍增器——其机动性与火力成功牵制了敌方主力,同时支援步兵完成侧翼包抄。面对日军无情的攻势,默里-莱昂所部溃不成军,最终获准撤往牛仑的第二道防线。然而为时已晚的撤退却因通讯系统瘫痪而陷入混乱,日军坦克与步兵趁势攻入日得拉无人防守的街道。其攻势不减,继而攻占亚罗士打机场,“发现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食堂内的粥尚有余温”。虽在强渡巴塔河桥梁时遭廓尔喀来复枪团的部分兵力击退,但此次挫败仅是暂时性的——翌日,由坦克开路的日军部队再度南进。他们通过夺取完好无损的补给堆集处与遗弃车辆弥补了后勤短缺,既维持又加速了向新加坡的推进。
日军坦克在日得拉防线的战斗中取得成功有几个原因。首先,佐伯中佐展现了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愿。其次,被派往马来亚的印度部队以前从未遭遇过坦克。第三,英国和印度部队丢失了许多无线电设备,因此无法协调防御。第四,日军快速的推进速度意味着防守部队总是处于被动反应而非主动应对的状态。第五,可以说最重要的是,当时英国观点认为坦克不适合丛林战。在日得拉使用的日本九七式中型坦克本应极易受英军马蒂尔达和瓦伦丁坦克上配备的2磅炮攻击。不幸的是,对于英军指挥部来说,一辆这样的坦克都没有。缺乏装甲部队和足够的反坦克武器带来了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从北马来亚的撤退变成了被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部队所击败的崩溃。
1942年1月7日凌晨,日军部队冲垮了英联邦部队位于仕林河以北八公里处的直罗拉防御阵地。由于对直罗拉的崩溃完全措手不及,仕林河重要公路桥的守军无法阻止岛田丰作少佐(第6战车联队第4中队中队长)的十七辆九七式中型坦克和三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的推进。当岛田以主力攻击铁路桥时,由渡边定信少尉指挥的六辆坦克和100名卡车运输的步兵被指派去突击公路桥。
渡边大胆的突击特点在于他决定离开坦克,用他的军刀切断桥上炸药包的导火索。除了通过强攻夺取两座桥梁外,日军坦克还在克伦尼橡胶园达成完全的战术突然性,他们在那里撞上了两个正在路边吃早餐的英军炮兵连。当日军坦克驶离后,英军哈里森中校勘察现场时目睹了这样的场景:
弹药卡车和前车猛烈燃烧着,炮弹在四处爆炸,子弹噼啪作响。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像醉汉一样在坑洼的地面上颠簸,直到撞上一棵树翻倒。一位副官(哈特利中尉?)告诉我,他们当时在离公路200码的橡胶林里吃早餐,突然有人来报告说坦克已冲破防线。德劳特少校当即冲向公路命令两门火炮进入战斗状态,然而五辆日军坦克已然逼近,停在路上对着隐蔽处疯狂扫射

经过七小时激战,一个坦克中队、一个步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及一个步兵联队成功击溃了整个第印度11师。战斗中,阿瑟·哈里森中校险些丧命。虽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仍由衷赞叹敌军的专业作战素养:“这些勇士全然不顾孤立无援的险境,以鲁莽而英勇的决心击垮整支师级部队并攻占仕林河上的桥梁。” 发动坦克夜袭的决策既富想象力又大胆果决——这虽是险招,但正如孙子所言“敌不及拒”(军事行动迅猛致使敌方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夺取仕林河桥梁的成功确实瓦解了英军沿西海岸的整体防线。
阿瑟·珀西瓦尔中将试图恢复战场平衡的努力仅取得部分成功。沿着主干道从淡边向金马士推进的日军部队正沉浸在胜利狂热中。由于未预料会遭遇敌军,这些士兵甚至将步枪绑在偷来的自行车把手上。他们的冒进使其远远脱离了拥有坦克和工兵卡车的数百人主力纵队。看似一切顺利,但他们浑然不知自己被有意放过,安然通过了金马士河桥梁。当主力纵队抵达时,地狱之门骤然开启——桥梁被引爆,瞬间吞噬众多日军生命。待硝烟稍散,新南威尔士第30团第2营B连与第15野战团第2营C中队立即从隐蔽阵地用步枪和机枪开火。而遭伏击的日军纵队伤亡惨重,至少五百人阵亡。
由于缺乏足够的炮兵支援,伏击部队被迫撤退。到傍晚时分,日军工兵已设法修复了桥梁。日军纵队的幸存者现在得到了第11联队的部队和来自向田宗彦大佐的第1战车联队越来越多的坦克增援。当日军纵队沿公路向金马士移动时,领头的日军坦克遭到新南威尔士第30团第2营2磅反坦克炮的射击。在短暂而激烈的交火中,八辆日军坦克中有六辆被摧毁(第1战车联队第1中队中队长浜田勇男少佐阵亡)。在弗雷德里克·“黑杰克”·加勒根中校指挥下顽强的澳大利亚部队设法坚守了阵地24小时。在完成任务之后,加勒根的部队井然有序地撤退了。
指挥马来亚澳军的亨利·戈登·贝内特少将认为,在金马士河的成功伏击标志着战役转折点。他在《新加坡时报》的发言尤为乐观:“我军将士坚信不仅能阻滞日军推进,更将迫使其转入防御态势。”然而这种乐观严重误判了战局——贝内特既未察觉日军坦克部队对战局的颠覆性影响,也未意识到战役正迅速脱离其掌控。1月16日,麻坡镇及其港口在日军的毁灭性空袭后陷落,印度第45旅的所有军官非死即伤。该旅残部沿海岸后撤数公里至巴力爪哇,而与此同时,日军则继续向峇吉里、巴力士隆与峇株巴辖无情地推进。

▲马来亚总指挥官珀西瓦尔中将与澳大利亚第8师指挥官贝内特少将,在马来半岛战役期间建立了极不成功的指挥关系——贝内特准确判断出珀西瓦尔无力应对与日军的苦战,可悲的是,他却未能意识到自身作为指挥官的缺陷

▲这张摄于1941年2月的照片记录了贝内特与印度第11师指挥官默里-莱昂少将(右)会晤。由于英军未能部署有效的反坦克防御工事,印度第11师曾两次遭日军小型坦克部队击溃。经历这些惨败后,默里-莱昂被解除指挥职务
次日,一次试图从巴莪分三路夺回麻坡的行动在第一道防线旅的部队遭遇了伏击。第二天清晨,西村琢磨中将下令发动自己的三路推进,由五反田重雄大尉(第14战车联队第3中队中队长)指挥的九辆九五式轻型坦克担任先锋。五反田希望效仿渡边在仕林河桥上的大胆壮举,并且怀着这个想法,他鲁莽地主动提出在没有步兵支援的情况下率队冲入峇吉里。负责此次行动的大柿正一少佐(近卫步兵第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对五反田这种机械化版“自杀式轻骑兵冲锋”心存顾虑,深知敌军极可能将野战炮改为反坦克用途。虽有这些顾虑,指挥部仍决定按五反田的计划实施无步兵支援的进攻——因为现有兵力更宜用于包抄澳大利亚第8师侧翼并在其后方设置路障。

▲日军九五式轻型坦克在马来亚战役期间对持续追击撤退的英联邦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莱恩·帕代尔·法雷尔在其著作《马来亚1941-1942》中描述道:“日军以惯有的强势和迅捷——但也带着席卷马来半岛以来养成的过度自信——发起了进攻。” 五反田的坦克部队欲抵达峇吉里,必须穿过一条两侧密林丛生、堤岸较高的狭窄路堑。当他的坦克爬升坡顶开始下坡转向路堑时,很可能已经注意到由查理·帕森斯中士指挥的反坦克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完全没有发现克莱里·桑顿中士指挥的反坦克火炮——该炮组已被精心隐蔽在橡胶种植园边缘。随着“呔嗬”和“那家伙来了”的呼喊声,穿甲弹与高爆弹的混合火力瞬间撕裂了五反田的坦克部队。
造成实质性破坏的是高爆弹——穿甲弹往往只会击穿九五式坦克的薄装甲一侧,再从另一侧穿出。据现场目击者本·哈克尼中尉描述,五反田的坦克被“彻底摧毁、燃起烈火、化为废铁且无人生还”。山下奉文将军在官方记录中宣称五反田大尉及其部下“光荣战死”。第25军作战参谋辻政信中佐在其战地记录中复述了这一评价:
1月16日至23日,一场殊死搏斗爆发。五反田的坦克中队损失了所有坦克,幸存官兵徒步发起进攻,抵达敌方炮兵阵地和巴力士隆桥,最后一位官兵在阻击敌人一段时间后阵亡……
五反田坦克中队最终被追授集体勋章。然而任何荣誉都无法让这些士兵生还。近卫师团战史后来以更平实的笔触记载了他们的结局:“勇者之命,徒然消殒。五反田的进攻失败源于四个原因:其一过于自信且可能嫉妒渡边部队的成功;其二选择让坦克沿未经侦察的道路推进;其三发起攻击时缺乏步兵支援;其四既已在金马士遭过伏击,本应预判并制定应对类似埋伏的方案。

▲此为澳军第4反坦克团第2营装备的2磅反坦克炮。1月18日,五反田坦克中队协同日军近卫步兵第4联队沿峇吉里公路冒进时,遭遇两门反坦克炮(图中即为其中一门炮组)在步兵支援下协同作战,最终击毁八辆坦克,迫使日军攻势受阻

▲如图所示,日军坦克纵队的首辆坦克为九五式轻型坦克。该坦克被击毁,乘员全员阵亡
在金马士和峇吉里作战中遭受重大坦克损失后,日军坦克部队被迫重新整编。因此,继续向柔佛南部推进的日军部队不得不暂时在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行进,直至获得新的装甲力量补充。随着英联邦军队持续撤退,日军工兵部队持续展现惊人的工程能力,迅速修复了被炸毁的堤道和桥梁。
与此同时,在东海岸地区,兵力不足的第18师团于1月21日攻占了兴楼。此次推进的代价惨重,在获得增援补充满员之前,该部队无力突破澳军在双溪默辛防线师团运送兵员与物资的护航船队在距兴楼三十公里处被发现。随后的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珊奈特”号驱逐舰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吸血鬼”号驱逐舰在英澳空军洛克希德哈德逊式轰炸机、霍克飓风式战斗机和维克斯维尔德比斯特双翼轰炸机的空中支援之下,对日军运输船及护航舰队发动攻击。尽管遭遇猛烈防空火力,两艘运输船仍遭轰炸,而飓风式战斗机则同时对滩头阵地进行扫射。但日军舰船无一沉没,急需的兵员和补给物资最终完成登陆。获得兵力补充的第18师团开始筹备对双溪默辛的进攻,却很快取消该计划——因为他们发现澳军部队早已脱离接触,正朝新加坡方向撤退。

在争夺柔佛海峡的作战中,山下奉文麾下的三个师团始终紧追不舍地跟在撤退的英联邦军队身后。事实上,在七周时间内,他的部队已跨越约1100公里时而艰险的地形。其军队还屡屡在作战与战术机动上胜过敌人——彼时英军指挥体系已日益显露出疲软态势。尽管如此,即便第18师团现已满编,山下所能调动的兵力仍仅约三万人。更关键的是,他受限于严峻的后勤补给压力,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采取经过精密计算的冒险策略。他对新加坡进攻的基本方案,仍是沿用曾在马来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战术。时间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补给状况决定了长期围困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日军步兵与九七式中型坦克向吉隆坡市区推进。该型坦克配备57毫米主炮及两挺机枪,对缺乏反坦克训练和准备的部队极具毁灭性——正如其在两次对阵印度第11师时展现那样。但在后续与准备充分的澳军交战中,日军装甲部队的作战效能则大打折扣
截至1月30日,日军先头部队已推进至距新加坡仅三十公里的古来。翌日清晨,阿盖尔郡及萨瑟兰郡高地人团的风笛手吹奏着凄厉的曲调,宣告着盟军向新加坡孤岛的最终撤退。8:15时,连接大陆的堤道被炸毁。身处柔佛苏丹绿色宫殿总部的山下奉文,此刻正清晰地眺望着新加坡北海岸。2月1日,他对军官们自信宣称:“此地乃殉国良所,我军必胜无疑。” 这番演说与其进攻计划一样,都充斥着虚张声势的成分——深知炮弹储备短缺并且可用坦克不足二十辆,他的目标是以最小代价迅速夺取这座岛屿要塞。
传统军事判断认为,日军跨越柔佛海峡的进攻必将来自东北方向而非西北区域。珀西瓦尔就始终坚信日军主攻目标将是堤道以东的海军基地,并通过指挥链下达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死守命令。其实早在1月20日,韦维尔将军就曾指出:日军更可能会选择堤道以西植被茂密的地带,该区域远离已调转炮口指向内陆的海岸炮群。在韦维尔看来,山下奉文绝无可能在战事后期放弃其制胜战略,转而将主力集中于东北战线——这完全不符合战术逻辑。
2月8日20:30时许,约十六个突击大队的先头部队开始向西北海域渡航,正好印证了韦维尔先前的预测。至次日凌晨1:00时,日军已建立稳固立足点并准备向前推进。拂晓时分,第5和第18师团主力及大量炮兵部队已全部渡海。傍晚时分,未参与主攻的近卫师团部分兵力在森巴旺海军基地附近海域实施横渡。从巨型储油罐中喷发的燃烧原油导致近卫师团的官兵出现部分伤亡,但攻势仍未受阻。他们的坚持很快得到回报:克兰芝防线缺口使得近卫师团主力及其炮兵、坦克部队几乎未遇抵抗便顺利登陆。与此同时,日军工兵即将完成以木结构重建堤道的工程。就在堤道被炸毁仅两天后,日军卡车与坦克已开始横渡在这场战役中完工的第251号桥梁。
就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山下奉文加紧攻势,这场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旨在加速被围要塞内守军士气的崩溃。他下达的“猛击速攻”命令得到完美执行:步兵和九五式轻型坦克部队突入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武吉知马村。2月13日,山下将司令部迁至附近的福特汽车工厂,随即命令第18师团攻占亚历山大兵营,第5师团与近卫师团夺取麦里芝蓄水库和兀里抽水站。随之而来的战斗异常惨烈,尤其在麦里芝蓄水库地区,日军坦克在击退英军第55旅至快乐山路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次日,日军持续施压,经过数小时白刃战,最终攻克226高地与山,击退了顽强抵抗的守军。与此同时,沿亚当路推进的岛田大佐麾下九五式轻型坦克部队成功突破武吉布朗坟场,向加利谷山与亚当园突进。
次日清晨,珀西瓦尔召集高级指挥官举行军事会议。虽然理论上仍可背水一战,但由于淡水供应已落入日军之手,加之需顾及百万平民的安危,投降成为唯一选择。16:45时,珀西瓦尔偕数名参谋军官驱车前往山下奉文司令部。这位被称为“马来之虎”的日军将领急于在珀西瓦尔察觉己方兵力劣势前完成受降仪式。经过珀西瓦尔一番拖延周旋,投降书最终于19:50时签署——山下奉文此刻无疑如释重负。

在日本,政府宣布将为每个家庭配发特别的“胜利配给品”——两瓶啤酒、一包红豆,以及为十三岁以下儿童准备的焦糖粒、糖果和糕点。新闻界也推波助澜,用夸张的标题让民众对胜利规模产生错觉: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朝日新闻》头版通栏标题宣称“太平洋战局已定”。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部长大平秀雄大佐对新加坡守军投降表示欣喜,并宣称:“美英两国应当审视日本三千年辉煌历史。我郑重宣告,随着新加坡陷落,战争大局已定。”为强调新加坡作战的胜利,日军在守军投降次日举行了阅兵仪式,代表现代化与国家力量的坦克方阵成为阅兵式的核心亮点。
正如阿拉里克·瑟尔教授在《装甲战争:军事、政治与全球历史》中指出的那样,坦克在极短时间内“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逐渐成为决定最终胜利的关键特质的象征。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随着传统新闻媒体逐渐被新闻纪录片取代,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迅速认识到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潜力。他们通过精心编排的阅兵仪式——往往出动数百辆坦克——拍摄影像向民众展示国家的军事实力。日本虽然引进坦克时间相对较晚,但很快就意识到了其宣传价值。
2月16日展示的日本装甲力量,既旨在震慑落败的殖民主义者,也明确宣告日本已经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对英国而言,新加坡的灾难性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走向衰微;对日本来说,这证明东方民族不再是二等公民。可以说,坦克正是日本崛起中最具冲击力的象征之一——尽管在日本控制下广袤“共荣圈”领土上的民众眼中,坦克已然化为了压迫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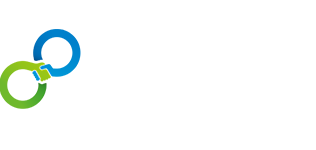
 2025-10-10 20:53:08
2025-10-10 20:53:08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